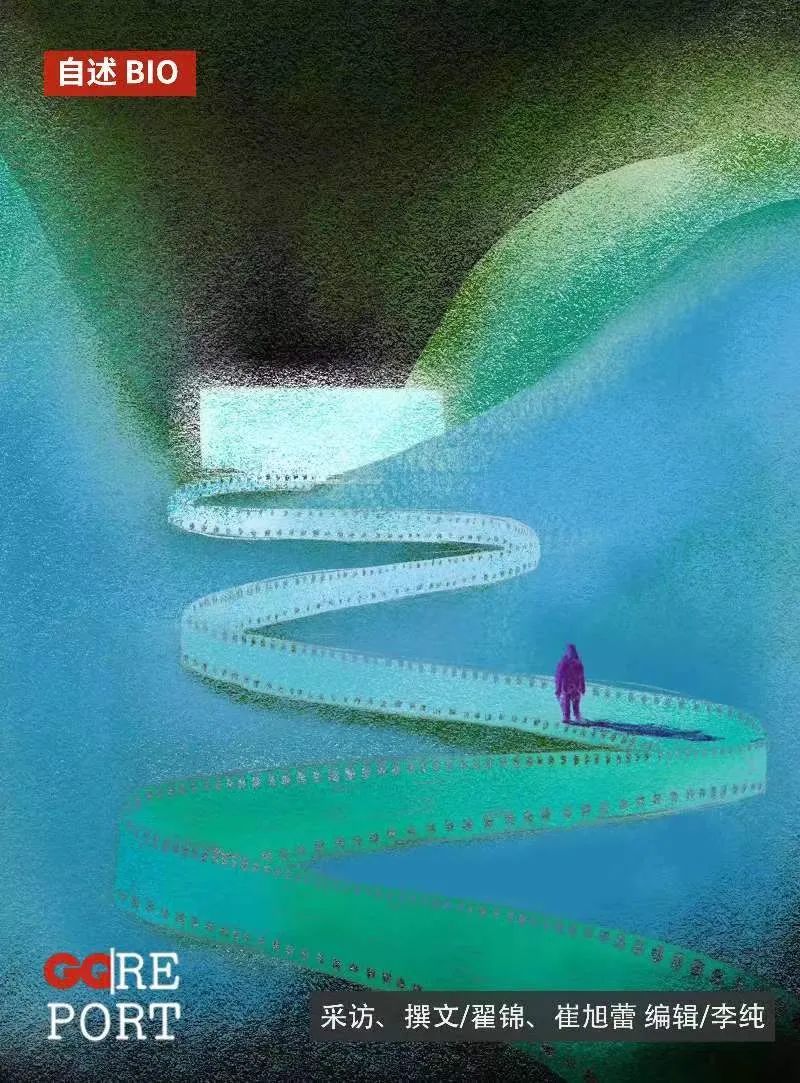
5月14日,戛纳电影节开幕,这届戛纳是久违的华语大年,有多部华语电影入围戛纳的不同单元。
作为三大国际电影节之一,戛纳电影节聚集了最著名的导演、最红的明星和最多的媒体。1993年,陈凯歌的《霸王别姬》获得金棕榈奖,1994年,葛优摘得戛纳影帝,到娄烨、贾樟柯等第六代导演,戛纳一直是中国电影向世界展示的最重要的舞台。近几年,一方面是华语电影在主竞赛单元的缺席,另一方面,几乎每年都有华语短片入围戛纳并获奖,从一个侧面体现出新生代创作者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我们邀请了参加过戛纳的10位电影行业人士讲述他们和戛纳的故事。什么样的电影能够获得戛纳的青睐?在戛纳看电影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中国电影和戛纳的关系是什么样的?这些故事不仅仅关于电影节,也关于个人的野心和梦想。
徐宽(Fred Tsui)

1994年,我首次踏足戛纳,除了疫情那几年外,每年都无间断地出席。最初我是为了看电影自费出席的,后来我开始为中国香港的杂志及报纸写戛纳的评论文章,每天看至少五六部电影。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开始负责替中国香港电讯的互动电视购买电影版权,在戛纳看到心仪的电影时,会跟中国香港一些电影发行公司联系,叫他们买下电影版权,再把VOD(即视频点播)的版权卖给我。
后来,我去了寰亚电影公司当总经理,主要负责亚洲电影的海外发行。我在寰亚电影工作了21年,身份由买片变成卖片,可以名正言顺去戛纳做海外发行的工作,虽然电影看少了,人脉却有增无减。鉴于我跟戛纳的负责人非常熟络,大家志同道合,当他们尝试首次放映类型片时,来找我帮忙,我便顺理成章地把杜琪峰的《大事件》推到戛纳去。英语有句谚语叫“and the rest is history”,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这部电影那年在戛纳亮相。
到戛纳的三十多年中,当然有很多有趣的事情。最初因为要忙碌看电影,废寝忘食,所以每次影展完毕后腰围都减了几寸,后来从事卖片工作,应酬多多,每晚大鱼大肉,影展完毕后腰围都会增了几寸!戛纳除了电影外,电影公司搞的派对也非常到位。在寰亚工作期间,我们有一回在沙滩搞派对,还请来不少好莱坞的名人出席。当我跟一位女同事交谈时,我发现派对入口出现了一位非常出名的好莱坞导演,他的眼神一直朝向我们。
我对那位同事说,导演看中你了,她说没有可能。我们还没有说毕,那位导演已经站在我们面前,他对我的同事说很欣赏她的演出,她的每一部电影他都有看,谁知道她压根不是演员呢,如此低层次的pick-up lines(搭讪)如果出现在他的电影中,肯定会劣评如潮。以后我每次看他的电影时,总会记得他当时的模样。
结束在寰亚电影的工作后,我成立了自己的顾问公司Moebius Entertainment,替海内外公司做顾问,除了继续做老本行的海外发行及影展推广外,也会为不同电影翻译字幕及剧本,到世界各地做影展评审,还有替国泰航空做访问节目。与此同时,我也是中国香港电影发展基金的委员,负责几个项目的督导工作。总而言之,只要跟电影有关的有趣工作,我都乐此不疲。
杨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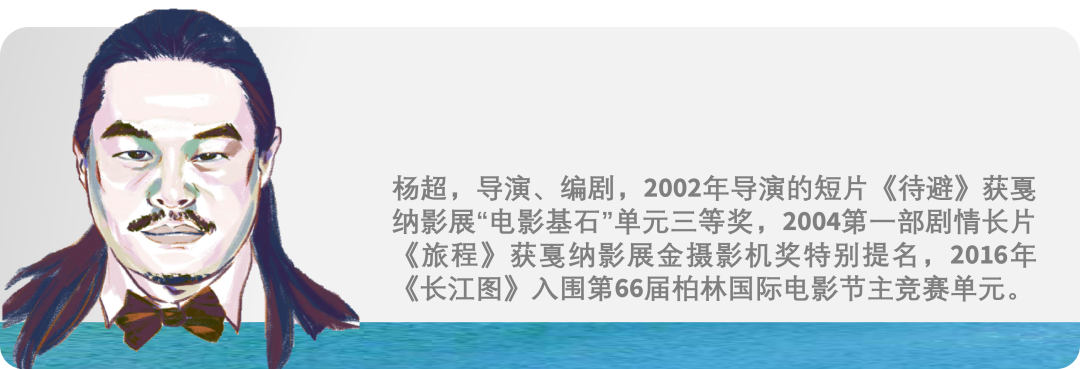
我很感谢戛纳和选片人,如果不是他们在一大堆电影学院的作品里把我选出来,给我精神鼓励和金钱鼓励,我也不会那么快开始拍第一部长片,我是完全被戛纳推起来的导演。
1997年,我拍了毕业作业短片《待避》,但是我没想过要去报名戛纳,感觉戛纳是一个特别遥远的、神话一般的地方,没有渠道,没有信心,我不觉得我拍了一个可以去戛纳的电影。直到2001年,戛纳的选片人到电影学院选片,他通过电影学院的老师找到我,说我的短片入围了戛纳。
从电影学院毕业后,我一直在北京漂着,做些小活,拍一些专题片,我特想有机会拍广告,因为能挣钱,但我没门路,我不太混圈子,生活比较闭塞。我一直感觉自己没学会拍电影,所以毕业后我还处在学生状态,一半的时间都在北京图书馆看书。我压根没想过拍电影,我觉得短片拍得还很差,《待避》除了有一个老师说不错,其他老师和同行都没觉得好。
我第一次听到毫无保留的赞美就是在戛纳,在宴席上,当时的主席吉尔·雅各布和选片人跑过来,一左一右,把我当小孩一样,抱着我说:宝贝你是个天才,你一定要再来,你一定要继续拍,拍完之后你要再回到这里来,这是你的家。我当时挺感动的,我说至于吗?他是电影节的主席。当然他可能跟每个他觉得需要等待的导演都会这么说,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在北京很少听到这样的话,大家比较理性,同行之间也比较难赞美对方。我后来在行业里说导演之间最关键的就是互相赞美,别人拍得好,你要说他拍得好,这样行业就发展了。因为新导演往往是最需要信心的人。
戛纳就像一个导演之家,他们把所有来的导演当成归家的小孩一样,给你充电。这是一个很难忘的旅程,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好的电影,所有人把电影当作很神圣的东西,你做出的微小的努力,别人都当作大事情。虽然我是短片导演,但是他们每个人都对你抱有期待,都鼓励你继续拍下去。
按照当时电影节的惯例,只有3天的酒店和居留时间,我就问戛纳,我希望可以住满全程,我要看电影。他们立刻就答应了,也给我解决了翻译。戛纳很贵,每个导演都可以在一个咖啡馆吃东西,虽然只有冷餐和简餐,但我把那儿当成了食堂。他们看我一直去咖啡馆和麦当劳吃饭,就给我一堆酒店的餐券,让我去酒店吃正餐。他们希望导演受到照顾,不希望你因为生活问题而不舒服。
虽然三大国际电影节也会竞争大导演、大明星的片子,但我认为他们最核心的竞争是谁能发现这个地球上最有创造力的新导演和新电影,这是戛纳的生命线。戛纳有着全球最商业的电影市场,这个市场也给戛纳做艺术片的底气,那里是一个近乎艺术电影的堡垒,它能对抗意识形态、权力、金钱,只看导演的创造力。
对我很重要的是入围基石单元有奖金,三等奖大概是5万法郎,这对我帮助很大,大约两三年我可以不用怎么干活,只是继续看书和看片,安心地准备剧本。2002年我从戛纳回来,2003年就开始拍长片。
但那时候国内对戛纳不太关注,我得奖之后,只有《南方周末》宣传过一个小文章,得不到太多的帮助,后面的导演就好很多。
我当时拿着《旅程》的剧本找了很多人,后来是田壮壮导演决定帮我,找了世纪英雄公司做出品方,给了300万,但后来钱用完了,没法做后期,壮壮导演说,我们也没钱了,你要不然用电影厂的剪辑车间。那是用手摇剪辑的方式剪,不需要钱,我就在电脑时代退回到了胶片剪辑,在巨大的车间里,用手里上百卷的胶片剪完了。
2002年我第一次去了戛纳之后,选片人时刻盯着我的新片,他也盯着很多别的导演。他说你要有第一版给我看一眼。我们没法输出录像带,我就找了一个小DV,在我们剪片车间的放映厅里对着屏幕拍,自己盗了自己一版,给他送过去。他很快就回信说非常好,他非常喜欢。但长片的入围没那么简单,要经过三四层的委员会选拔,他说这个版本太差了,能不能给我更好的版本,我需要给大委员会看。
我说我现在没有更好的版本,但是如果你能给我一封热情洋溢的戛纳来信,我也许可以去说服投资人,让他们继续给我钱做后期。他说没问题,他真给我发了一封邮件,我把那封信打印出来去找壮壮老师,他拿去给世纪英雄的领导看,那时候电影已经超支了,他们就挤牙膏一样给了一摊子钱,每一次通过一层选拔,选片人就发一封更热情洋溢的信,我打印翻译出来去跟领导要钱,直到最后一次选拔,我们才做出了拷贝。
2004年4月1号,愚人节那天,选片人给我发邮件说《旅程》入围了“一种关注”单元,你的片子我们非常喜欢,你值得这样的荣耀,你第一部长片能够在“一种关注”单元,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2004年,杨超的《旅程》入围戛纳
他也问我在戛纳有没有发行方,我说没有。那时公司没人管,也没钱,只给我买了去戛纳的机票,选片人帮我推荐了很好的发行方,但因为公司停止运营,最后《旅程》没能在海外发行,没有影响力,也拖后了我拍下一部片子的时间,为了募集资金,隔了7年我才拍《长江图》。
2005年戛纳开始办创投工作室,我拿着《长江图》的剧本去了戛纳,在欧洲进行融资,得到了5个创投的帮助。后来在拍摄的时候,因为中途没钱了停机一年半,一直到2015年9月份才做完后期,那时戛纳已经结束了,离我们最近的是2016年2月份的柏林电影节,我们把片子投给了柏林电影节,经历了三四轮的反复选拔,在我生日那天得到了入围的消息。
面对去柏林还是等戛纳的艰难选择,由于片子战线拖得太长,制片人和投资人快崩溃了,我们对戛纳也没有绝对的信心,尽管我前两部作品都入围了,但是戛纳很多次把非常著名的导演一脚踢出去,比如得到过金棕榈奖的库斯图里卡,所以我不敢冒险,如果被戛纳拒绝,又错过柏林,再等一年的时间压力团队没法承受。经过短暂的考虑,我们决定去柏林。
《长江图》在柏林放映后,很多朋友跟我说你这个适合戛纳,你应该等戛纳,我说那也没有后悔药,没办法。每一部电影有自己的运程。
黄璐

收到《盲山》入围的消息时,我上大四,22岁,正在电影学院看电影,我打电话给之前在剧组认识的设计师定做一套礼服,他起名“一树梨花压海棠”,上面有很多手工刺绣的梨花和小鸟图案,水白色的小礼服,我配了一双绿色的鞋,我爸还买了好多藏银,让我戴着,另一些当礼物送人。当时也不知道可以要赞助,我都是自己花的钱,一万块,我拍这部电影的片酬也是一万块,所以我爸叫我“黄一万”。片酬都花在买礼服上了,还得自己买机票。
当时我们剧组有人在吵架,为什么你带的衣服比我多,是不是故意抢风头,马上搬出去,直到首映礼开幕半小时前还一直在吵架,我一边画眉毛一边听着他们对骂,我快疯了,我也不知道怎么面对这种争执。
我们还约着开车去摩纳哥,那里有赌场,离戛纳很近,但车里又有不愉快,半路上我经纪人让我见徐克,我说我要回去了,他们把我丢在半路上,我带着DV机,一路走一路拍,一路问火车站在哪里,就像《憨豆先生的假期》一样,自己还挺高兴,到了火车站看不懂法语,到处找会英文的法国人,当地很多都是老人,最后碰到一个当地的年轻人,就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他也去戛纳,那些海报都是他们贴的。他跟我说,火车晚点了一个多小时,我就跟着他走,我没有地址,把酒店的照片给他看,他说正好离他挺近,把我送了回去,这是我在戛纳的一个冒险,就像憨豆先生横冲直撞,但运气比较好。
第二天我知道他们去摩纳哥的路上出车祸了,他们说都是因为我走了才导致车被撞,修车钱要AA。我挺痛苦的,人生地不熟,我很想走,去哪里都好难,大人的世界好复杂,又贵,又没时间吃饭,每天吃三明治感觉吃不饱,我就很想赶紧回成都吃东西。
是制片人孙小姐救了我,我就只跟着她,不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天天带我见人,参加party,我每天晚上穿着同一套礼服,就跟灰姑娘的水晶鞋似的,只要一穿上那件裙子,别人就开始夸。
她带着我去电影市场,她在开会,我坐在旁边吃冰淇淋,她也给我安排采访。我每天穿着高跟鞋跑来跑去,我们约着去看金基德的《呼吸》,张震主演,但孙小姐忙得忘了时间,我们去晚了不让进场。
后来我挺开心的,长了不少见识,见了很多人,我也见到偶像侯孝贤,还有张曼玉。很多世界顶尖的电影人在你身边,忽然觉得电影梦没有很遥远。
在戛纳,我认识了我现在在纽约的经纪人,一直到现在我们还在合作,我们之间没有合同,但是比合同还要长久,就像家人一样,她看完了《盲山》专门来找我。
我还认识了一个斯里兰卡的导演维木希·加亚桑达拉,我们俩是在戛纳的街上认识的,那里有一家特别有名的酒吧,大家举着酒杯在街上喝酒,满条街站满了电影人,我碰到他,他说他要拍一个新电影,他可以加一个中国女生的角色,我说好吧。
当时就这么一说,第二年我还真的去了,也挺刺激,2008年斯里兰卡在打仗,每天都有士兵拿枪检查我们的车,组里没有别的中国人,大年三十的时候导演带我去吃了顿中餐,就算过年了。我爸觉得危险,还拜托一个朋友陪我去,我们住在海边殖民政府盖的酒店,挺浪漫的,她去动物园玩,第二天那个动物园就被炸了。后来我们的片子《世界之间》入围了威尼斯主竞赛单元。
第二次去戛纳就放松很多,很开心,自己能做主了,认识很多朋友,感觉如鱼得水,我还带了调料做火锅。我也已经知道有赞助,直接在现场找礼服,各个品牌的礼服随便选,根本不用自己花钱,人家还倒给你钱。珠宝也是赞助的,上红毯前戴上,走完就在厕所摘下来还给保安,我轻轻松松进去看电影。走红毯前要吃饱,看完电影出来都半夜了,我也不想光走红毯不看电影。有的模特就是为了走红毯,走完从侧面就出来了。
每次去戛纳都感觉要累得脱一层皮,白天各种活动、采访、拍摄,晚上各种party,得有两个人轮班陪我,白天经纪人,晚上化妆师,她们说我是特种兵。
第三次去戛纳很特殊,《六欲天》入围了戛纳的“一种关注”单元,导演祖峰因故没来,我去了但是不能在我自己电影的首映上露面,我被几个人围着进去。

2019年,黄璐主演的《六欲天》入围戛纳
第一次去戛纳对我影响很大,我觉得这个世界很大,有无限的可能,你一定要走出去,而不只是局限在国内演偶像剧,你会有更宏大的目标,这个目标你见过,摸到过。虽然回来后有一些落差,总觉得去戛纳之后会有一些不一样,但回国之后发现还是一样的,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那一年好像都没戏拍,但也很快都调整好了,在脚踏实地地拍一些东西。
每次去完戛纳都像充了电一样,又知道自己要继续向哪里努力了,还有很多人真正知道电影到底是什么,为了什么。无聊或者怀疑自己到底在干嘛的时候,就会想还有那么多好的电影人和作品呢。
去年,我又见到了斯里兰卡导演,他从年轻小伙子变成了大叔,胡子都白了。
马雷梦

2010年左右,我在上海电影节认识了一个以色列导演,他拿了很多DVD给我。他的很多作品在三大国际电影节获奖,我们可以引进你的电影,那时国内视频内容平台需要批量购买正版电影。
第一次去戛纳,我是和优酷合作,我们给优酷推戛纳获奖片,优酷负责内容的人说要去戛纳,他是第一次去,怕有点不熟,问我要不要去,我入行只有一年,我都不清楚戛纳有最大的版权市场,跟大家一样,以为只是电影节,我快速研究后就去了。
从小我在电视上看戛纳的海和红毯,法国电视台每年5月份都有戛纳专题,一个娱乐综艺节目把演播室搬到了戛纳的海边,明星嘉宾都会参加这个节目,走红毯、接受采访。第一次去现场很激动,我还跟爸妈和朋友说我来戛纳了,但电视里很璀璨的红毯,因为一直有人走来走去,红毯没有明星和灯光的样子也很平常。同时也会感觉我很渺小,因为那里聚集了全球电影行业的人,他们看上去很自在,到处都是熟人。

2023年,马雷梦在戛纳
那时我不知道什么电影在中国市场有价值,但至少大家都认可戛纳等电影节,我们就做了一个获奖影片的版权打包,主要是金棕榈奖影片,也有最佳剧本奖、最佳演员奖等主竞赛片。国内刚开始购买版权,价格不高,我们和法国公司说,反正怎么也比零好,这都是新的收入,而且买的片子也多,我们作为中间公司一边筛选获奖片,一边和国内的公司聊,我们要保障引进的外语片最少能卖两三个网站,如果只有一个平台想买,我们就不做了。我是第一个引进侯麦电影的人,我是他的影迷,很开心能引进他的片子。
一开始我卖版权给视频平台,后来我开始引进片子上国内的院线。在戛纳开幕之前,你就要提前约好各个版权公司的时间,一天约五六家公司开会,每个会30分钟,看他们的新片单,我们判断片子在国内能不能过审,有没有市场,这是很繁琐的工作,很多片子不适合中国市场。这些片子有的还在制作中,就看剧本,拍完了他们给你发链接,或是有的在戛纳首映,你就直接在现场看,入围主竞赛的片子竞争很激烈,销售公司会看大家的报价。
戛纳是一个交易市场,只不过卖的是电影,跟卖皮鞋也差不多。这些公司在戛纳电影宫里都有展位,小公司几平米,大的公司有50平米,分成好几个房间,有电视屏幕,贴着大的电影海报,有的公司觉得在电影宫里摆站台不够高级,就在周边租一个可以看到海的房子。作为买家就很累,十一点半在电影宫开完会,12点之前要看导航找到另一个地方,你只要迟到一次,后面所有的会都迟到,虽然赶路的时候能看海,晒太阳。
再后来,中国电影有走出去的需求,我开始做卖家,帮他们在海外电影节做推广宣传,往外卖中国电影,我在戛纳电影宫有了展位,每天约买家开会,争取把中国电影的版权卖给各个国家的发行商。做销售最重要的是你代理什么片子,我们得在国内找好的项目。
有一年,我代理了一部片子,没有入围戛纳,但是片方想在戛纳办发布会,片子在国内6月上映,他们去戛纳的海边拍照,我邀请外媒和国内媒体,安排发布会,素材返回国内做宣传预热。那时候做娱乐的国内媒体都会去戛纳,但现在中国媒体去的少了。
好莱坞的一些片子也会在戛纳举办大型推广会,因为戛纳电影节是全世界媒体数量最多的活动,如果你足够有吸引力,媒体都会帮你传播,当然媒体更重视入围戛纳的片子。有时我代理的片子没有知名导演和演员,对媒体吸引力不够,只有出品方比较吸引人,我就邀请一些行业媒体给这些高管做专访。现在有的电影入围了但不是主竞赛,都不好拉媒体。
我们的合作方之一是戛纳最大的活动公司,他说他们工作的核心就是讲故事,其实观众也不是很清楚到底谁入围、谁没有入围以及入围了什么单元,你只要把故事讲好就行。大家看的都是明星照片,其他细节不重要。当然之所以可以这么做,也是因为戛纳比较高级,有热度。
我现在是卖家,不需要再去看电影选片了,但我每一年在戛纳都会去看一次电影的首映场,穿西服走红毯。我表妹住离戛纳不远,她有次来找我玩,让我给她安排一张首映礼的电影票,我们想了各种办法,花了5个小时才找到合适的票。在戛纳路边,从早上6点开始就有人拿着纸,纸上写着各种各样好玩的哀求,比如如果你给我今晚8点的票,我把房子送给你。看首映礼的体验很好,大家站起来鼓掌,第二天杂志上就会写这个片子观众鼓掌有4分钟、6分钟或8分钟,鼓掌时间的长短,是片子受不受欢迎的评价之一。
张海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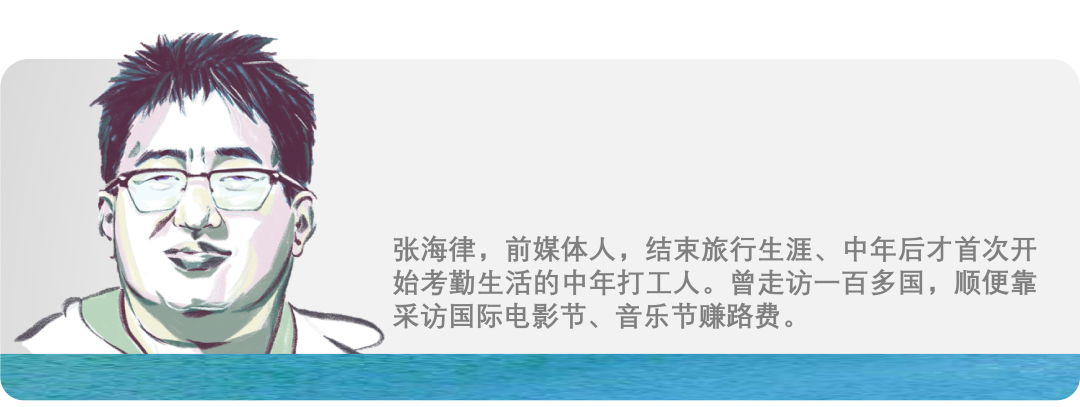
我去过戛纳电影节两次,一次是2012年,一次是2014年。最后一次去戛纳距今10年了,因为年代久远,我的经历可能不算是特别有代表性。
作为腾讯的“编外成员”,我在电影节负责的是采访报道和写评论。身为编外人士特别幸福,我可以任性地去采访一些很偏门的导演,比如东欧那些“斯基”和“维奇”,不像公司自己的记者们,需要去机场接机,采访一些国内的明星,以保证网站的流量。我当时是特别自由的。
有些采访需要和影片的公关方提前联系,有些采访是到了现场再约。在戛纳电影节,PR公司们会在重要的酒店外“摆摊”,你可以去那里结识他们,和他们大概约一个采访的时间段,再由他们分配具体时间。后来就逐渐演变成PR们拥有自己的邮件群,记者报过名后,他们会给你群发邮件,通过邮件来约访。
有件事情还挺搞笑的,2014年戛纳的一个中午,我打开Gmail邮箱,收到了一封邮件的催问:“你在哪呢?”我才知道对方以为我约好了法国演员马修·阿马立克的采访,却临时失约了。我那时很懵,因为头天晚上我收到的邮件是:“不好意思,安排已经满了,希望你理解。” 他们第二天怎么又莫名其妙地来催我了?由于时间已经过了,那个采访最终也没做成。戛纳就是这样,计划总不如变化快,除了我这种乌龙事件,因为临时变动,约好的采访做不了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电影节期间,张海律去往戛纳外海的两个小岛
在戛纳电影节当然有采访大牌明星的机会,但这些采访常常需要租赁场地,不管是艺人的经纪,还是片方的PR,都会把场地的租金费用分摊给记者。有些采访需要付钱,碰到乔治·克鲁尼这些的超级明星,甚至要付一千欧元(这个数字应该没有夸张)。我记得当时有几个大的门户网站相互竞争,就真的有一家舍得砸钱,最后得到了15到20分钟的采访机会。
我自己做的采访里专访群访都有,有些相对小众的导演是专访,比如德籍土耳其裔导演费斯·阿金,我很欣赏的一个法国的吉普赛导演托尼·加列夫。采访后者时,我们随便约在了一个海滩的酒吧,聊了大概半小时,那是我在戛纳采访时间最长的一次。
多数主竞赛影片安排的采访时长往往在15到20分钟内,现场会有来自世界各国的六七个记者,一人问一个问题,观察到创作者说得差不多时,记者就赶快去抢下一句话。如果你稍微害羞一点,或是语言表达上稍慢一点,可能连提问的机会都没有。
还有些素材可以在场外获取,在以前,你可以申请一个媒体柜,柜子里堆满了片子的物料,这些印刷品还挺漂亮的,常常记录着剧情简介、导演阐释之外的更多信息,比如影片外景地资料。我记得2012年的戛纳,我还别出心裁地把看的所有电影的外景地整合成了一大篇文章,比如《利维坦》的取景地有个鲸鱼骨架在那儿。这个比较突出,也有好多凑数的,比如一个家庭故事,非要凑一个外景地,现在想来也有点牵强。
三大电影节我都去过,如果说具体的区别,虽然青菜萝卜各有所爱,但在戛纳,片子质量会在一个平均水准之上,不像威尼斯电影节、柏林电影节可能会跳出让你一辈子难忘的作品,但也有大跌眼镜的电影。
陀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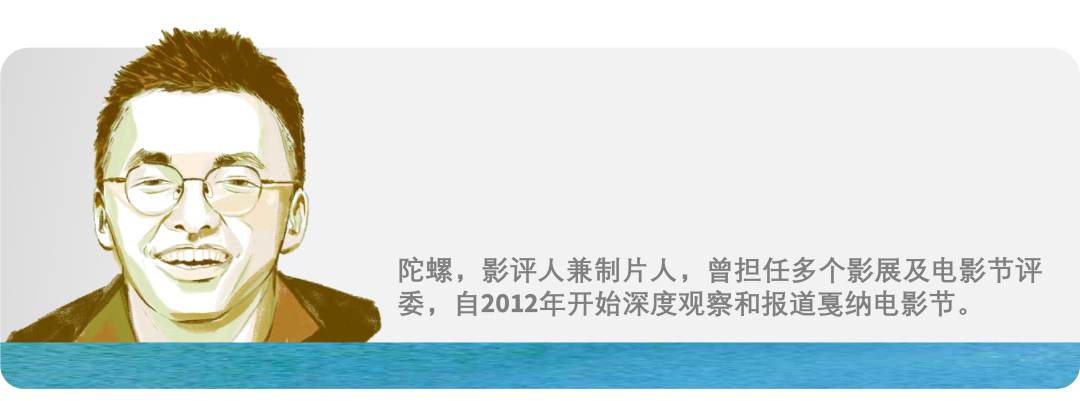
我最早一次去戛纳电影节是在2012年,自那之后,除了2020年、2022年,我每一年都去过。
去戛纳的前两年我拿的是蓝色证件,证件等级不高,基本上每部片子都要排队一两个小时,赶上热门电影,则需要排队两三个小时起。5月份的戛纳会在晴天和雨天间来回切换,有次排队赶上雨天,我整个人在室外淋成了“落汤鸡”。不只是我,所有排队的人都淋湿了。电影开始后,整个影院里弥漫着一股像是毛巾打湿后闷起来的味道,闻着很恶心,即便如此,大家还是安安静静坐在那儿看电影。
这就是戛纳电影节最大的魅力,也是会让人上瘾的一个东西,你在那儿会感觉到所有的人都是热爱电影的,电影是真正受到尊重的。虽然说到底只是看一部电影而已,整个电影节充满了看电影的仪式感。
为了营造这种仪式感,官方也制定了很多规则,比如证件的等级制度,不同颜色的证件代表着不同级别,以此决定观众观影的先后顺序。这里面当然会有一种很虚荣的、很不好的东西,但另一方面,它会让你觉得看电影是一件有优越感的事情,这也是仪式感的一种。
戛纳电影节还有一个著名的规定,就是红毯首映场会严格地要求每一位观众的穿着,比如女性必须要穿高跟鞋,男性要身着全身西装。这个我还吃过一次亏,在电影节,我持有的是媒体证件,看的基本都是媒体场,穿着休闲即可,并不需要正装。去戛纳两三年之后,我还是想去感受一下走红毯的感觉,所以那次专门带了正装和一双皮鞋。
到了走红毯那天,我先是用媒体证件换到了红毯票,又回到住处换了衣服,换完马上跑回去排队,整个人大汗淋漓。终于排到我上红毯,保安叫停了我,说我的鞋子不合格,“你穿的是褐色翻皮皮鞋,不是正规的黑皮鞋。”我就没能进去。从那次之后,我再也没有为了去走红毯进行过任何专门的尝试。

陀螺在戛纳
在戛纳十年,每年我至少会看35到38部电影,最多可以看到50部,平均每天能看4到5部。映后观众席的反应基本就这么三种,骂街的,掌声雷动的,以及同时有脏话,同时有掌声的。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特别喜欢骂脏话,有时电影还在滚片尾字幕,影院灯光还没亮起,大家都没有离座,就听到一个意大利人用巨大的声音骂了一句,“什么傻x电影啊,烂电影”。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观影过程中爆发的掌声,在戛纳电影节,大家观影时还是持有相对严肃的姿态,在中途爆发掌声的概率是极小的。其中有两次印象很深刻,一个是泽维尔·多兰的《妈咪》,影片画幅是正方形,在电影的中后段,男主角突然用双手扒开了画幅,那个镜头特别震撼,当时全场发出惊叹声,之后开始鼓掌,那个感受我至今都记得。另一个是《托尼·厄德曼》,中间有一段高潮戏,大家一边爆笑,一边鼓掌,观影氛围特别热烈。
与此同时,在戛纳电影节,看电影时睡觉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如果谁跟你说,我从不睡觉,要么是TA看电影太少了,要么就是TA骗你的。我印象里最晚的一场电影在11点,那部电影好像3个小时。每个有证件的人都是有工作的,有时候看电影看到凌晨两点钟回去,还要写东西到三四点钟,同时第二天早上八点半还有一场,这中间只有不到4个小时的时间可以睡觉。这样的生活要持续10天,而且每部电影几乎都是大闷片,如果你一边只睡4个小时,一边看完阿彼察邦看蔡明亮,看完蔡明亮又看毕赣,那4个小时就不顶用了。
那种睡觉不像我们平常打瞌睡一样,先闭上眼睛,之后酝酿一下,再慢慢地进入睡眠,睡意往往发生在眨眼的瞬间,可能前一秒你还在觉得:“哇,这个电影好好看”,但一眨眼睛,下一秒就失去意识了,你完全不知道自己睡着了这个事情,非常可怕。
电影宫内设有很多咖啡点,提供浓缩美式咖啡,大拇指大小一杯,咖啡点前全天排满长队,所有人都在狂灌咖啡。但我觉得这并不那么有效,真到了眨眼就睡的那种状态,喝多少咖啡都没有用。我想了很多不让自己睡着的方法,现在每年去戛纳,我都会提前准备一包糖,变态酸的那种,或者其他刺激性的食品。有时候看一些很重要的电影,但真的快要睡着了时,我会吃东西,或者马上去上个厕所。还有一部电影,我看了大概20分钟之后,跑到了最后一排,站着看完了整部片子。
有时候我甚至会为了睡觉去看电影,早上看完第一部电影已经很累了,但下午还有一场很重要的电影,万万不能在那时睡着,这时候怎么办呢?可能在这两部电影之间,我刚好还安排了一部电影,那就先去看看这部电影好不好看,如果前五分钟我觉得它不好看,就马上转头睡去。
在戛纳电影节观影真的特别辛苦,有好几年我都累到中途感冒发烧,整个人崩溃,但还是觉得太快乐了。因为在那十二天之内,戛纳给你营造了这么一个泡沫,置身于泡沫中,你24小时内的所见所听所感、脑子里面处理的所有信息,只与电影相关。就好像在这十多天里,你去到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
这也导致很多人,包括我在最开始几年会产生一个戒断反应,俗称“戛纳后遗症”,从戛纳回来之后,大概有那么个一星期,人会觉得很空虚。因为之前在戛纳,电影的氛围实在是太浓缩了,人也太紧绷了,突然“啪”的一下把戛纳这个源头切断了,人乍一回到现实世界里面来,一下子就不知道接下来要干嘛。
戛纳电影节当然也有很多缺点,比如一些制度上的问题,比如它的“森严”的等级,最开始以朝圣者的心态去往戛纳的时候,我并不了解,去了10年之后,这些问题我看得更透彻了,但也不会因此导致不喜欢。对我而言,反而是你越了解这个电影节,就更喜欢它。
魏书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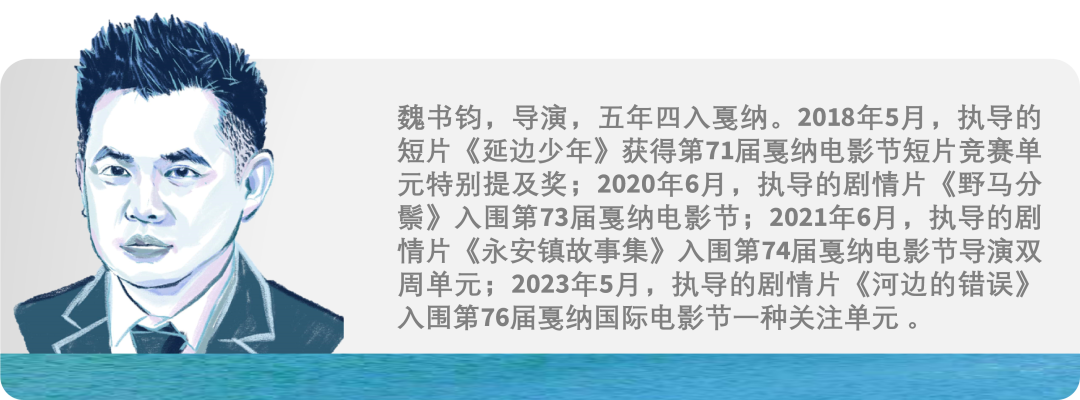
2017年做创投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导演双周单元的审片人,我们见面时,我拎了两盒龙井打算送他,他说我不喝茶,我说没关系,就是客气一下。《延边少年》入围戛纳电影节后,我第一反应是那两盒茶叶发挥了作用,但我的影片入围的是官方单元,和导演双周是两个选片系统,我才知道不是因为茶叶。
收到入围通知那天,我正和摄影师还有一位联合编剧讨论《野马分鬃》的剧本,三个人实在想不出来招了,就去打篮球,入围邮件是打完篮球后看到的。在原定计划中,晚上应该继续聊剧本,结果到了咖啡厅,剧本一字没提,我们电脑也没拿出来,而是一直在讨论去戛纳穿什么衣服。戛纳在海边,度假风,我们就整了一些特别漂亮的短裤,到戛纳后发现一是太冷了,二是去任何场所都需要穿正装,这些衣服通通没用上。
一直以来,我都没想过得奖这个事儿,觉得片子能够入围已经是中彩票了,这次来戛纳就是旅游的。颁奖前一天,电影基石单元和一种关注单元开始颁奖,导演申迪的《动物凶猛》得了基石的二等奖,我们心想说哎哟,大家身边终于有一个年轻导演得奖了,这才开始有了得奖的期待。
颁奖那天,有个流程是所有短片导演一起走一遍红毯,我收到了工作人员打来问人在哪的电话,才发现自己把集合时间记晚了半个小时,于是迅速飞奔到电影宫,勉强赶上了红毯。走完红毯后一位工作人员特地对我说,“刚才大家集合的时候说了一下,你没听到,我再跟你说一声,待会儿短片有两个奖,第一个奖叫特别提及奖,不用上台,站起来招招手就可以了。第二个奖是短片金棕榈,要上台发言。”
我没有多想,觉得就是补充嘛,过一会儿碰到了一个负责选片的工作人员,又跟我重复了一遍,我才觉得一会儿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奖啊?到了颁奖环节,第一个宣布的是我的短片,我满脑子都在想到底有没有奖,听到得奖后还挺懵的,获奖感言更是压根没想。
回想起这一次去戛纳,我觉得自己就是一名小学生,有那么多优秀的前辈和同龄人在这里,一定要多多学习,珍惜每一次交流的机会,后来越去戛纳,我越觉得还有太多要学习和进步的地方。
我入围了戛纳电影节四次,实际只去过两次。《野马分鬃》入围那年,戛纳由于疫情没有办成,《永安镇故事集》入围那年,我因为有别的工作安排就没前往戛纳。我录了视频向现场的观众和电影节致以问候。演员黄米依和剪辑指导马修作为代表出席了首映式,他们第一时间收到了很多现场观众的掌声和认可。
甚至黄米依在卫生间里也收到了一份热情洋溢的观影反馈。一位阿根廷女观众跟她声情并茂地描述她有多么的喜欢这部电影,原因在于她是一位阿根廷的球迷,她在片尾听到了《阿根廷请别为我哭泣》这个音乐。虽然因为这个原因喜欢这部电影是我们始料未及的,但这也让我更加意识到,每个观众都会从个体的经验出发去看一部电影,有大量而丰富的个体经验会进入到一部电影当中,通过观看,再作用到观众心里,电影某些时刻成为了人们与自我沟通的载体。作为一个电影工作者,我感到很幸福。

2023年,《河边的错误》入围戛纳,魏书钧(右)和朱一龙
去年携作品《河边的错误》去往戛纳时,同样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戛纳电影节有一个传统,就是一种关注单元的主创除了会参加影片在白天的映前红毯外也会参加当晚首映的主竞赛影片的映前红毯,这被视为一种更大的殊荣,也是对影片和主创更广泛的一次曝光。每个参加红毯的剧组,可以选择自己的红毯音乐。我们选择了《河边的错误》这部影片里反复出现的《月光》作为红毯音乐。但不知道为何原因,我们走红毯的时候并没有放我们的音乐。直到那晚红毯的最后,导演马丁西科塞斯率领《花月杀手》的剧组走向电影宫时,《月光》的音乐才悄然而至,年迈八十的马丁导演缓慢而坚定地在红毯上行进着,全球媒体的摄影机正聚焦着红毯上这位杰出的艺术家,仿佛是一种注目礼。
时至今日,我也无从查证,为何那天的音乐播放是这般的,但这何尝不是一种美好的意外呢?
单佐龙

全世界的电影产业都在不断萎缩,电影销售情况低迷,华语电影就更难卖了。在以前只要电影进入三大国际电影节(戛纳、威尼斯和柏林),就有助于海外发行和本土市场的销售,但现在因为各种原因,几乎只有戛纳电影节才有明显的作用,你的电影只有在戛纳才能被看到、关注、买卖,只有戛纳才更有机会把它变成一部世界级热门的作品。
4月第二周戛纳举办发布会,5月戛纳开幕,如果你的电影想去戛纳,你就得在安排制作周期时提前考虑戛纳的时间。但是你知道计划赶不上变化,电影制作永远都在变化,比如拍摄会暂停,剪辑会卡住,一卡一两个月,剪不出来就是剪不出来。
2018年3月初我们决定要送《地球最后的夜晚》去戛纳,毕赣的压力很大,他需要在3月底拿出一个能过关的版本,用于戛纳选片委员会看片。4月1日凌晨,他总算交上了,凌晨5点,我拿着刚制作完成、还温热的硬盘坐上去法国的飞机。
送片的版本还没有完成ADR和3D转制,戛纳电影节评委都是火眼金睛,做不做后期对他们没那么重要。但入围之后就要为了在戛纳上首映去赶后期制作,这肯定是要花更多成本的,有时候项目预算不足也没办法做到。
我在巴黎待了半个月等消息,等片的同时我一直在跟三个法国公司开会讨论,我们应该如何去影响戛纳选我们的电影,如果被选进了戛纳我们要做哪些准备工作。戛纳的委员会非常精英,铜墙铁壁,没什么人可以真正影响他们,但如果在他们做抉择之前,能有一些意见领袖包括影评人提前看到影片并传回他们的看法,对他们而言是有参考性的。戛纳艺术总监福茂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他说:“一到做总结的时候,每个人便马后炮式地对主竞赛单元来一次重新的编排——这种时候,根据已知的受欢迎程度,要作出一个理想化的排片表实在轻而易举。这不过是总结结果而得到的一场幻觉。”这其实说明了,戛纳也在揣测某部电影是否会受欢迎,他们的选择是否正确,所以说戛纳选片能否被影响?能,只是这个空间很有限,也并不是大家都能这么去办。如果影片在入选戛纳前就确定了国际销售公司尤其是法国本土发行公司,这也会加重戛纳选择影片的信心。
我记得我们坐在一张长桌上,我一个中国人对着10个外国人,我的英语没有那么流利,他们责难我,为什么电影没做完?为什么现在还没交上?所有的事情汹涌朝我而来,我要一件件反馈给国内不同的团队让他们解决问题,与此同时,团队在焦虑地做后期:电影都做不完,你还来问我这些东西?
整个过程是很焦虑的,我很担心电影完不成制作,我不想空手而归,想给大家一个交代。有一天我在巴黎老旧的地铁站里走着走着就哭了起来,出了地铁站,毕赣给我发来一条微信:“佐龙,明天回来吧,去不去戛纳,不重要。”
戛纳是全世界最拽的电影节,其他电影节有可能会提前几个月给你发offer,但戛纳都是提前一个礼拜甚至两三天才发offer,不管你是新人还是大导演,所有人都得等。对于中国片,既有制作上的压力,也有制度上的要求,我们必须有龙标才能去境外参赛。很多去戛纳的电影(包括欧洲片)都不是最终的版本,在戛纳结束之后还得继续做后期,甚至还要改剪辑。
我们终于等到了电影入围戛纳“一种关注”单元的消息,我立马从巴黎飞回北京。但我们的压力更大了,要在一个月的时间完成最佳剪辑版本,大家不眠不休地接力工作,回想起来是噩梦。
做法语字幕的时候,片子的中文字幕还没做好,于是我们就出一句中文字幕翻译一句法文。5月8日戛纳开幕当天,我们还没交上片,我抱怨赶不上戛纳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毕赣的愤怒也累积了很久:“烦烦烦,你有什么好烦的,我现在连电影都剪不出来!你还想怎么样!”
如果我们赶不上,这将是一次严重的事故,但我更清楚的是,过不了毕赣自己这一关,电影送不出去。我知道毕赣导演的特点,他一定会在最后一刻把东西交上,而且会交得很完美,但在这个窗口期你依然很紧张,而且我作为制片人要对各种事情负责任,比如一个入围电影去戛纳必须办after party,怎么办、在哪里办、什么时候办、谁出钱?我们有三个PR公司,分别负责中国媒体、法国媒体和英文媒体,你得协调好时间,你说头疼不头疼。
后期工作走到最后第二步的时候,大家已经精疲力竭了。毕赣和调色师唐强在工作棚里剧烈地争执,他希望唐强能休息一会再工作,不要无效劳动,唐强暴怒:“我哪还有时间休息!我再休息,你们就都别想带拷贝去戛纳了!”“那我就不去了,我不要去什么的他妈的戛纳,我需要你拿出最好的质量来!”
为了将随时有可能输出完成的拷贝以最快速度送至戛纳,我们缜密地制定了一个代号为“葫芦娃”的方案,每隔两到三个小时左右,将一名工作人员送上去往法国的飞机,把所有人的出行时间平均分布到最后的两天时间内。
5月12日傍晚,第一颗放映拷贝送达戛纳,但那个出现制作失误,无法使用,非常崩溃。5月14日下午2点,毕赣终于带着重新输出的第二颗拷贝,昏昏沉沉地来了戛纳,在5月15日凌晨2点通过了技术测试,同一天上午11点《地球最后的夜晚》在戛纳举行媒体场首映,幸运的是我们办到了。

2018年,福茂迎接毕赣导演和几位演员上台
放映结束,我回到公寓房间,看到同事正在吃力地用谷歌翻译拼命地刷着推特,忽然,他疯了似的呐喊起来:“炸了!炸了!‘地球’炸了!牛逼,龙总,你看,他们说我们导演牛逼!”
戛纳就像是一部电影的火箭发射站,如果你对一部电影有足够信心,你一定要把它带到戛纳去。《地球最后的夜晚》入围戛纳的“一种关注”,虽然没有得奖,但我们在影评人的评分榜单里排名前十,戛纳让全世界电影行业里的精英分子第一时间看到这部电影,有了口碑,并把电影带去了世界各个地方。
陈剑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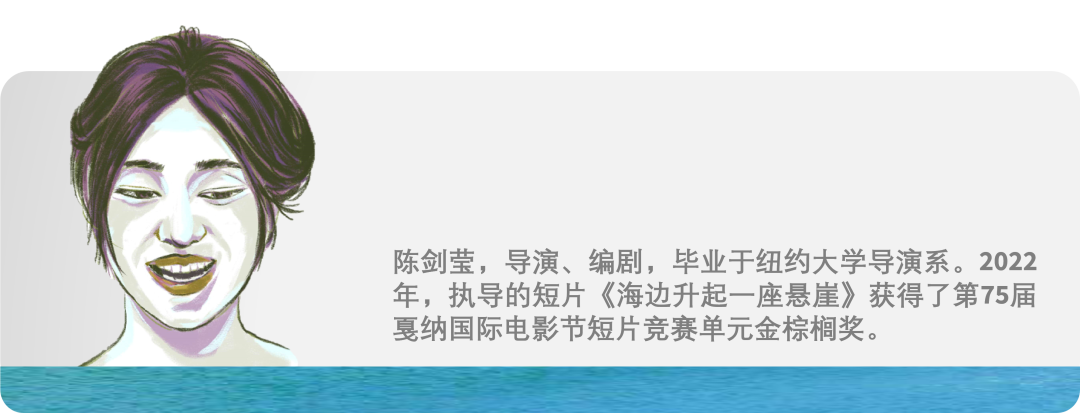
我完全没想过《海边升起一座悬崖》会入围戛纳。
短片是2021年12月底拍完的,在那之前,我的上一个剧情短片拍摄于2017年,两个片子之间隔了4年的时间。这四年内,我做了很多执行导演的工作,业余时间写剧本,还给各种影视公司提案,这些提案一个都没成。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被否定、被拒绝,没有任何正向的评价告诉我说我是可以的。
长久不拍片,导演会手生,拍完《海边升起一座悬崖》后,我并不知道自己的水平如何。我和制片人讨论片子要投递什么电影节时,觉得戛纳肯定不能进,于是提议说能不能投一些小电影节,稍微带点精神慰藉奖性质的就可以。制片人劝我说不要着急,等一等戛纳,你现在比较焦虑,就不要管这个事情了。我也相信他们,那就由他们去操作吧。
影片入围的消息让我非常非常惊讶。那天,我正在做瑜伽,收到制片人发来的消息后疯狂地在房间里蹦跳,我平时是很自律的人,基本不吃晚饭,那天破格点了一份东北炒粉作为夜宵。
能够入围已经很幸运了,影片得奖这件事情,我更是完全没有想过。
颁奖典礼上,主持人说的是法语,我戴的同声传译耳机里也会传来英语,两种语言我都在努力听,有点听混了。主持人念完“The Water Murmurs”(短片英文名)后,会场上开始鼓掌,全场掌声雷动,我隐约听到了我的名字,本能地怀疑了一下,应该是我吧?在这之前,没有任何人和我透露过得奖后该如何行动,我并不知道后面的流程是什么,当时整个人的状态十分慌乱,大脑一片空白。
由于事发突然,我上台时没有带手机,说完感言后直接进了后台,后面我陆陆续续地看到很多钦佩的前辈来到后台,没有办法合影,我就在那默默地看着。其实我挺想拿手机记录一下后台,没有记录到,有点儿遗憾。
等全套流程都结束之后,时间已经过去了两个小时,拿到手机时,手机“炸”了,所有的朋友都在给我发信息,微博上也不断涌出新的提示。那个时候我感觉自己真空了两个小时,回来整个世界都变了,光回复这些信息,我就处理到了大概凌晨三四点。我那时还在筹备我的新长片,需要跟国内的团队开会,处理完消息马上就到了开会的时间,所以我一直没睡,到开完会,早晨七八点那会才睡觉。
我妈应该是全世界最后一个知道我得奖这件事情的。颁奖的时间是国内的深夜,我爸妈都睡着了,他们醒了已经是早上,我妈问我说:“怎么了?有事吗?”我说:“没事,妈,我拿了个金棕榈。”

2022年,陈剑莹执导的短片《海边升起一座悬崖》获得短片竞赛单元金棕榈奖
拿奖后,大家的评价给了我很多力量。在颁奖结束后的那个afterparty上,评审团里面的一个女导演主动找到我,说看完片子后非常感动,她想到了她的孩子和她的孩子的未来,并走上前来拥抱了我,我也很感动,我们两人相拥而泣。我才知道,我想表达的关于人类和空间、我们的过去和未来,这些主题是真的被看到了。原来电影这个东西是可以跨越国家和不同的文化,直达人类的内心的。
那天我总共也没睡几个小时,但一直处在幸福中,就像是我当时发在朋友圈的一句话,“一个梦做十年可能真的会实现的”,是那种感觉。
如果用一段诗来形容那次的戛纳之旅,我会选择聂鲁达那首,“那段时光似乎前所未有/又似乎一向如此/我们去那里/一无所求/却发现所有的东西都在那儿等候”。这首诗和我当时的心境非常契合,去戛纳时,我一直是蒙的,我不知道评委们喜欢上了我什么,只觉得有个机会可以放映一下我的片子,还能和国际电影人交流交流蛮好的。但后面的收获真的让我觉得所有的东西都在那儿等候,不管是对自己的信心,对电影的热情,还是来自于全世界观众的爱和支持,所有的这些很温暖的情感,都在那个地方在等着我。这是我完全没有预料到的。
最近我在北京电影节的女性单元里也完成了一部新短片,叫《不如再见》,和《海边升起一座悬崖》讲述的告别不同,它讲的是一对恋人四年后重逢的故事。离别和重逢都是我现阶段的创作母题,我希望这些故事能打动更多的观众。
黄树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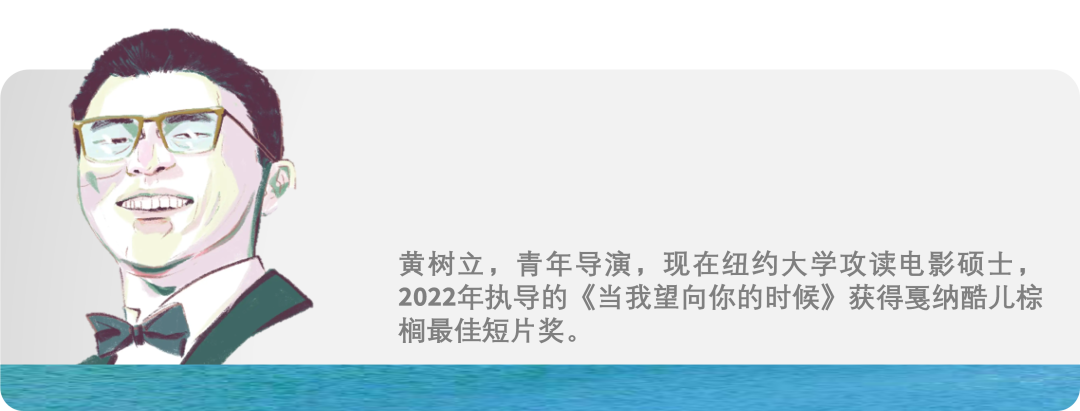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个电影节,在那之前我感觉自己不会和戛纳有什么关系。
收到入围消息的时候,我刚结束一个剧组的工作,凌晨4点我迷迷糊糊突然醒了,看了一眼时间就看到了入围邮件。很激动,睡不着了,我开始给朋友打视频分享这个消息。但开心不了多久,就要忙着给片子做法语字幕,调色,做声音,准备一堆材料,要做海报、媒体手册,处理各种流程上的事情。
2022年去戛纳的中国人比较少,我也是经历了一些困难才出来,4月份,我从温州去四川办的签证,本来买的从北京去法国的机票,但那时候北京疫情突然爆发,我觉得可能出不去了,又把北京的航班取消,改成从广州飞的航班,那一天广州刮台风下大雨,差点感觉走不了了。
到了巴黎,朋友跟我讲要不要租一套燕尾服,因为电影宫晚上的放映都要求穿正式礼服才能入场。我想我这辈子也没穿过,就买了一套,后面所有的场合也就只有这一身,一连穿好多天。
每天我都在看电影,一天看三四场,很开心。电影宫的放映太隆重了,在影院坐下之后,荧幕上会实时转播主创团队从红毯走进来,再走到最中间的位置,给观众行礼,再熄灯,电影才会开始。
电影节倒数第二天下午,我从电影宫看电影出来,收到一封酷儿棕榈工作人员的邮件,说当晚的颁奖典礼希望我能到场,他们说得比较委婉,但好像也给了我一点预告。我当时获奖时候说的话特别矫情,我说我一直以来都非常希望我妈妈能以我为骄傲,但我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我现在想想都觉得脚趾抠地,也可能跟语言和情境有关,用中文讲这些感觉太矫情,用英语讲就自信很多。大家鼓掌鼓得也很捧场,然后就一起去蹦迪,蹦着蹦着,第二天醒过来我就阳了,躺在床上没法动,躺了三天,昂贵的民宿又得续上。

2022年,黄树立得奖后
我觉得我可能去不起戛纳了,那里好贵,大家在那儿过得非常拮据,好多朋友都是几个人睡通铺,挤一个房间,但又要穿着燕尾服排队看电影,然后吃路边的小三明治。但也很开心,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大家都对电影都有很大的热忱,他们的作品也深深地打动我,你能找到很多知己。大半夜,大家从party里出来,一起坐在海滩边喝酒,是一些闪光的回忆。
我后来去了柏林电影节,对比很明显,戛纳像在三亚办的,柏林像在北京办的。一个是旅游城市,一个是正常运转的大都市。你在柏林电影节能感受到整个城市的魅力,你能看到在城市里生活的人,在戛纳只有电影,小镇那么小,所有人都是来参加电影节的,你在任何一个酒吧,旁边聊天的人都是电影工作人员或发行商。
入围戛纳是一个肯定,但其实离我已经太遥远了。我之后又回了学校上学,这件事好像是课间休息的一个插曲。我就是从门外路过,往里面看了一眼。
采访、撰文:翟锦、崔旭蕾